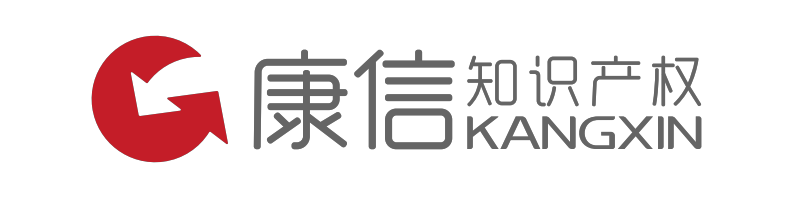《专利法》第22条第5款规定,“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在该定义中包含三个核心要素:
时间标准:以专利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为界限,早于该日期的公开信息构成现有技术。
地域标准:采用绝对新颖性原则,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公开,均可能构成现有技术。
公开方式:包括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其他方式公开(如口头报告、展览等)。
笔者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发现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经常会引用文献作为对比文件,用以评述专利申请的新颖性或创造性。
文献作为现有技术的几种典型情形包括:传统印刷期刊、电子文献(其是通过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等互联网数据库收录)、预印本平台(如arXiv、bioRxiv)。
其中,传统印刷期刊作为连续出版文献的形式,其通常定期发行,如每月、每季度或每年。故对于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等期刊,确定其文献的具体公开日期往往难以准确。而当针对文献的公开日期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极为接近时,准确确定文献的实际公开日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申请人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若发现引用的文献公开日存在问题,可以在答复中提出异议,若异议被审查员接受,则该引用的文献将无法作为现有技术。
下面将以一件笔者处理过的案例为例,分享下针对此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以下将具体的申请人名称用申请人A代替。
申请人A的某项专利的申请日为2020年6月17日,审查员于2023年4月29日下发了该项专利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并在该通知书中引用申请人A在《深空探测学报(中英文)》中发表的一篇文献,该文献在中国知网CNKI中记载的发表日期为“2020年6月15日”,审查员将该发表日期视为公开日,并基于该文献,以创造性缺陷驳回该项专利的申请。
在本案中,审查员直接将CNKI数据库中记载的“发表时间”认定为该文献的网页发布时间。
然而,笔者了解到,CNKI这类互联网数据库中显示的“发表时间(一般指编辑部的发行时间)”与“网页发布时间”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时间概念,其定义对比如下表所示:
概念 | 发表时间 (Publication Date) | 网页发布时间 (Web Release Date) |
法律依据 |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 2.1.2.1 |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签名法》 |
典型载体 | 期刊印刷版、会议论文集、书籍 | 数据库平台、期刊官网、预印本网站(如arXiv) |
确定性 | 通常有明确的版权页或刊号记录 | 依赖系统时间戳,可能存在技术误差 |
因此,笔者认为审查员不能直接认定本案中所引用的文献的电子形式在“2020年6月15日”这一时间点处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状态。
另外,不同学报有不同的出刊方式,如《深空探测学报(中英文)》在截至案件审理之时一直为纸质刊,且编辑部并未授权互联网数据库“优先出刊”该学报的电子形式(具体可与编辑部负责人员进行了解)。因此,在互联网数据库上检索的发表日期应是对该文献纸件出版发行内容所进行的收录时间,纸质刊应为该文献的最先公开方式。
在本案中,与纸质刊公开日期相关的时间信息有如下两条:
纸质刊上记载的时间为“2020年6月”,因此,根据《专利审查指南2010版》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1节规定的“出版物的印刷日视为公开日,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开日的除外。印刷日只写明月份或年份的,以所写月份的最后一日或所写年份的12月31日为公开日”。因此,基于上述依据,可推断该文献的公开日期为“2020年6月30日”。 在互联网数据库上检索结果页上给出对比文件的发表时间为“2020年6月15日”,而考虑到互联网数据库上收录纸质刊出刊所公开的文献的发表时间可能存在如下三种情况: 情况(1):纸质刊的实际发行日期; 情况(2):互联网数据库与编辑部就发表时间所约定的日期; 情况(3):纸质刊中未显示具体出版发行日期时,互联网数据库根据内部规则进行规范化处理后的日期,常直接设置为某月15日。
而对于上述所说的情况(3),由于其实际的公开日期并不对应,因此,不能将“发表时间”直接认定为该文献的公开日期。
另外,需注意的是,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出版刊期(即“刊物封面上显示的日期”),如:周刊是一个月出4期、旬刊是一个月出3期、半月刊是一个月出2期、月刊是一个月出1期。
在本案中,结合对比文件在《深空探测学报(中英文)》的学报封面上记载的内容—“2020年6月份文种变更为中英文,双月下旬出刊”容易得知,“2020年6月15日”是根据投稿日期以及“双月下旬出刊”这个出刊时间规定,直接推断该文献的公开月份为6月,具体公开日期为下旬开始的第一天,即15号。但该6月15号这个日期并非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状态,故不能将该时间直接认定为该对比文件的实际公开日期。
综合考虑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比文件中的实际公开日期并非互联网数据库上“发表时间”所记载的“2020年6月15日”。因此,可以认为所引用本案的对比文件不能作为评述本专利的创造性的现有技术。
对于代理师来说,在面对此类情况时,应根据关于公开日认定、证据规则等专业知识,收集关于纸质刊的出版信息、数据库收录规则等相关证据,精准确定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和审查员提供论证中的不足(如公开日的认定是否准确、数据库“发表时间”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
在意见陈述书中,引用相关法律法规和证据,逻辑清晰地阐述观点,并结合具体证据进行合理推断,以支持其对公开日期的异议。如果审查员坚持原有观点,代理师应进一步补充证据或调整论证角度,例如引入第三方专家意见或数据库运营方的官方说明。
另外,对于申请人来说,在任何形式的论文公开前(包括投稿、会议海报展示、预印本上传),优先提交专利申请,建立“先申请、后公开”的绝对红线意识,确保申请日早于任何可能的公开渠道(包括互联网数据库),避免因公开时间差导致核心技术丧失专利性。此外,建议优先提交专利申请的同时,还应预留出缓冲期限,以应对审查补正等其他特殊情况发生。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对于存疑的事实,代理师应结合申请人提供的原始资料,从“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大核心维度构建针对性抗辩。在抗辩过程中,应明确注意文献的网络版与印刷版时间差,同时结合纸质刊官方出版政策佐证,核查数据库回溯文献的原始载体(如纸质刊馆藏记录),并善用审查指南“存疑有利于申请人”的解释空间。
专利制度本质是技术公开与权利保护的精密平衡,数字化时代唯有将证据思维贯穿研发披露全流程,方能在审查博弈中掌握主动权。